经过近半年的筹备,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和音乐学系共同主办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暨蔡仲德辞世十年祭”学术研讨会于5月10、1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成功举行。
5月10日上午9:30,“会议开幕式暨蔡仲德辞世十年纪念会”在琴房楼演奏厅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蔡先生的女儿、华纳音乐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冯珏女士,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郭淑兰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蔡先生培养的第一位博士苗建华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前党委书记陈自明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研究员,音乐学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和云峰研究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蔡先生的生前好友、同学、同事、学生、中央音乐学院师生等各界代表。会议由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教授主持。
郭书记首先代表学院致辞,对以探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和蔡仲德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主旨的学术研讨会的意义给予充分肯定,随后郭书记高度评价了蔡先生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学科建设所做的历史贡献,并深切缅怀了蔡先生敢于直言、刚直不阿的高尚人格。郭书记的致辞中特别提到蔡先生生前作为西城区人大代表尽心履职,为学院的教职员工的合法权益奔走呼号的事迹,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基层人大代表的责任和担当。
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随后致辞,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戴嘉枋研究员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表示,希望借此次会议一方面纪念蔡先生,同时也推进中国音乐美学事业的发展。戴嘉枋高度评价了蔡先生自身品格中所具有的士人格精神和他的学术研究中贯穿始终的人本主义精神。



蔡先生一生情系中央音乐学院,情系他所钟爱的音乐美学事业。他去世后不久,家人遵照其遗愿,向音乐学系捐赠了蔡先生多年珍藏的相关文史哲和音乐美学典籍,以及十万元人民币,以奖掖后学,学院为此专设“蔡仲德音乐美学基金”以纪念蔡先生。在蔡先生生前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乐曲声中,举行了庄严的捐赠仪式。周海宏、冯珏、和云峰共同揭开覆盖在蔡先生生前用过的书柜上的红色绒布,书柜里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的典籍似乎把我们带入了蔡先生的学术世界。和云峰宣读了音乐学系特意制作的捐赠证书,并郑重地将其送给冯珏女士。蔡先生的夫人、著名作家冯钟璞先生因年岁已高,不能亲临现场,特意为此次活动制作了一段视频,追忆了她与蔡先生相濡以沫的风雨人生,并感谢音乐学院为此次活动所做的一切。冯珏随后发表了现场感言,表达了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深切谢意。
中央音乐学院前党委书记陈自明研究员,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韩锺恩教授,中国哲学学会冯友兰专业研究会常务理事、南阳师范学院冯友兰研究所所长聂振弢教授,蔡先生生前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同事、中央音乐学院李起敏教授,蔡先生患病期间的主治医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张诗杰先生,蔡先生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苗建华,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女士分别从各个角度对蔡先生进行了追思。
蔡先生生前的教研室同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教授对本次活动高度重视,对会议手册的制作以及活动的议程亲自把关,给予了重要的指导。会议当天,王院长因为有公干在身,无法亲临现场,特委托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苗建华研究员现场宣读了他的书面讲话。在书面讲话中,王院长回顾了他与蔡先生基于学术而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美学教研室的优良风气。王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到:“蔡仲德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至今无人超越。后来他的研究转向更为广泛的文化领域,他对中国文化研究所提出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也多次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我始终认为蔡仲德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具有中国文人最高尚的品质和人格精神。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学术遗产,他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会永远载入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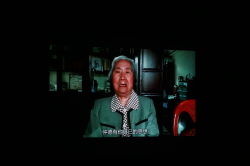



5月10日下午和5月11日全天,与会代表在教学楼401学术报告厅针对蔡仲德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进行了专题研讨。关于蔡先生的学术思想,研讨会主要聚焦于其人本主义思想,李起敏、苗建华、周海宏、邢维凯、冯长春、明言、张向东等均有言及,以下一并综合大家在这方面的看法。人本主义既是蔡先生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标。蔡先生认为文化包括音乐都是人的创造物,因此要从音乐与人的关系中去探求音乐之道,认清文化的本质。判断文化乃至于音乐价值的尺度应该是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在蔡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价值标准,由此出发,他对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乐为礼的附庸的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给予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对五四以来的新音乐道路,蔡先生基于人本主义的立场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指出中西音乐的区别不在民族性的差异,而在前现代与现代的分野。即便他的思想曾引发巨大争议,压力之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求道于西方音乐以重中国音乐。李起敏、冯长春还指出了“五四精神”在蔡先生人格塑造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何为“五四精神”,在学界一直有争论,教科书上也大多语焉不详。而“五四精神”本身若不能清晰界定,会影响到对中国现代史上诸多问题的评价。李起敏、冯长春提到,蔡先生首次提出要厘清两个五四:一个是文化的、自由的、宽容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激进的、排他的五四。而前者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分清两个“五四精神”,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史上的众多复杂问题提供了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冯长春更是直接指出,“五四精神”成为蔡先生学术研究与人格精神的根本。南阳师范学院冯友兰研究所王仁宇教授指出,蔡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集中在三个领域,分别是: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士人格以及冯学研究,蔡先生在这三个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士人格和冯学研究方面,蔡先生的研究已超越了音乐学的领域,在哲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蔡先生还是一位善于自省的学者,苗建华在发言中谈到蔡先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性,即对于音乐形态的相关知识的欠缺,因此他很少从音乐本身谈美学思想和观念,他希望他的这一缺憾能在学生身上得到弥补。关于蔡先生的著述情况,叶明春做了详细汇报,他还系统汇报了他正在进行的蔡仲德论文论著资料搜集、整理与录入的工作。李浩还在发言中着重谈及蔡先生“我注六经”及“六经注我”的治学方法,何艳珊基于中国古人的时空观念,通过《大梦敦煌》这部具体作品探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在现代音乐作品的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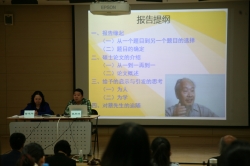




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议题中,学者们的探讨则涉及更为广泛的论域。礼乐是中国传统音乐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次研讨会有两位学者涉及这一课题。罗艺峰指出自西汉以来的礼乐规范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之上,在随后的发展中,随着理学大潮的兴起,礼乐逐步转向内在道德的自觉,至南宋朱熹,这一思想进程最终完成。王晓俊则基于商周图腾考察礼乐的始源,考证了“礼自乐出”的内在逻辑。古琴音乐历来被视为文人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徐上瀛的《溪山琴况》则为古琴美学的经典之作,谢嘉幸的发言以《溪山琴况》的当代阐释为例,试图让传统典籍在现代社会重放光彩。谢嘉幸基于对意识美学的反拨和对身体美学的弘扬,力图从心、情、意、眼、耳、鼻、舌、身等方面进行综合把握,从身体美学的视野完成对《溪山琴况》的当代阐释。宋瑾则以“自况”的行为方式对《溪山琴况》进行了解读。宋瑾认为操琴的目的不在娱人,也不在自娱,而在自况。何谓自况?自觉、自为、自勉、自助即为自况。比“琴况”而成就“人况”,遂为全士,即合道者。他认为当今世界,古琴精神若得以弘扬,必能冲淡世俗浊气。同样是讨论古琴美学,章华英则结合徐上瀛和严澂编订的琴谱,从演奏实践的谱法和指法角度探讨晚明虞山琴派“清微淡远”与“气韵生动”的美学特征。张伯瑜的发言也试图从具体的音乐形态特征探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美学问题,他指出中国传统器乐曲的主要结构关系有三:主题、自然音响的摹拟、连接,这三种主要关系体现了传统音乐中和而不同,既统一,又多样的思维方式。韩钟恩的发言根植于他一以贯之的立场,那就是对听感官事实的强调。他指出要将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和传统音乐中的美学问题进行有效区分(这一立场与邓四春的发言近似),在众多中国文人音乐程式与民间音乐习俗中钩沉古典范式的美学思想,并基于听感官事实为基点考掘传统形态的审美特征,以寻求二者同属中国的共性。牛龙菲则对中国古典音乐美学中的“行和”、“礼乐”、“动静”、“来去”这些范畴进行了新的解读,比如他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中的“和”并非“和谐”之“和”,而是“行运”之“行”;“礼乐”与宇宙万物的运演相关联。李曙明在发言中为他提出的“和律论”音乐美学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辩护,并提出传统音乐应与时俱进,在比较中借鉴超越创新弘扬。在项阳看来,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音乐并非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而有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如何不拘泥于传统音乐美学对审美维度的探讨,而着眼于考察中国传统音乐生存状态中的功能性因素而进行跨界作业,项阳的这一思考值得音乐美学界关注。周世斌呼吁音乐美学走出纯学术的高空作业,下放到传统音乐传承的实践活动中,在实践对策方面加以应对,在具体实践上加以指导。罗小平是唯一一位做过两场主题发言的学者,她认为蔡先生对中国古代音乐心理思想研究具有奠基、指引、示范和导向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古代音乐表演心理研究存在的若干问题:缺乏关注力度;缺乏范畴体系的构建;缺乏较广泛的中外比较视域和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互渗的视界;缺乏运用不同研究思路的准确性。本院博士研究生王学佳探讨了《声无哀乐论》产生的理论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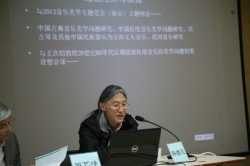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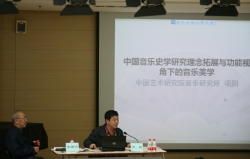



主题发言之后的自由讨论将本次研讨会推向了高潮,学者们就音乐美学的学科属性、学术边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始自项阳的疑问:在一个祭奠亡灵的场合,伤心的家属面对着丧葬音乐,能秉持一种审美的态度吗?项阳认为音乐这时候更应该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何宽钊同意项阳的看法,但认为这已经属于音乐社会学的课题。项阳认为这种限定会使音乐美学变得狭窄,何宽钊回应,从事音乐美学的人可以跨界从事音乐社会学的研究,但这个问题本身属于音乐社会学或音乐人类学,我们还是要明晰论题本身的学科属性。牛龙菲指出美学本身是一个误译,美学的本意为“感性学”,谢嘉幸认为不能把美学狭窄地理解为审美、欣赏,死者的家人面对丧葬音乐也会有丰富的感性体验,罗艺峰认为甚至丧葬音乐也有可能是欢快的。何宽钊则认为,即便讨论感性,面对这种音乐,死者家人、围观者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这种音乐一旦脱离具体的仪式进入舞台,观众的感受会更不一样,这些不同的体验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境分层处理,不能混沌化。张伯瑜强调学科还是要保持基本的限定,其边界不能无限制地扩张,否则就乱了。在激烈的讨论中,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体现了中国音乐美学界在讨论问题时既激烈又不失理性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气。自由发言阶段还讨论了音乐美学多元化等问题。



会议期间的5月10日晚,会议主办方还邀请了福建晋江木偶剧团在教学楼401举行了精彩的闽南音乐专场音乐会,体现了让学术与音乐实践相结合的会议主旨。
5月11日下午,“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暨蔡仲德辞世十年祭”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副所长宋瑾教授的闭幕词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