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王府大院音乐厅内乐潮暖流。
2010年11月24日、12月5日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成功举办了两场郭文景师生作品音乐会。郭文景作为当代中国乐坛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其所培养的作曲人才是未来——延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潮音乐”以来的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创作的生力军。以师生新作品音乐会的形式公开接受艺术圈内人士、甚至是社会艺术爱好者的谈论和品评,这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除此之外,作为庆祝中央音乐学院建院70周年之校庆系列展演活动的一部分,新作品音乐会目的在于向社会展现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教、演成果,也侧面透露出中央音乐学院致力于培养、造就新一代作曲家以及建设音乐人才储备的雄心和卓识。本文所涉及的两场音乐会,上演的作品多是郭文景师生们的近作,共计16部,多数为首演。及时向学界汇报最新成果、接受批评,对于推动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笔者完整聆听了音乐会,两场均为室内乐,但选排各不相同:11月24日为“郭文景学生作品音乐会”,侧重在读大学本科、研究生的近作,是为学生组;12月5日的“郭文景师生作品音乐会”侧重往届毕业生、或已留校工作、以及郭文景教授本人的新作,是为教师组。两场音乐会认真听下来,对于听者不得不说是一次考验,对于笔者而言,这是一次考察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创作、演出、受众的完整状态,思索学院派音乐作品创作机制的未来走向的很好的机会,收获甚丰。
一、
先谈作品。
尽管11月24日“学生组”音乐会作曲家为在校学生,但经过郭老师给予的系统、全面的作曲技能训练,却已显露出很高的艺术才华以及超出年龄的艺术上的成熟。正如郭文景教授在音乐会开始之前简短致辞中所言:“今晚音乐会的八位主角代表了八种个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都不模仿我”。学生不模仿老师,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学习和吸收优秀音乐文化成果,而这种艺术上的个性显露了作曲家可贵的品质——对声音敏感的捕获能力和艺术创造力,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音乐学院培养音乐人才的模式:严谨而不拘泥。
纵观音乐会上演的八部作品,就创作主题而言,大抵可分为“文化元素”与“情绪元素”两大类。前一类作品诸如六重奏《暮色巴林》(江辰曦 曲),不同于以往我们对草原文化的概念——诸如辽远宽广的抒怀、马背上民族的旷达等等,这首作品与这种固有的印象大不相同:以一个大二度加纯四度的核心装饰音动机为种子贯穿始终,以展现暮霭的缓慢而稳定的行板速度与急速的装饰音律动之间的张力,展现出内蒙古巴林右旗黄昏时分静谧的草原景色,充分发挥了管乐(单簧管、萨克斯与小号)、弦乐(小提琴、大提琴)跳跃的点描色彩以及作为持续音起粘合作用的手风琴的音色特点。三重奏《向斯特拉文斯基致敬》(金秋月曲)借鉴了斯特拉文斯基早期原始主义风格的作品,如《春之祭》、《彼得鲁什卡》等,显出那种打破平衡对称的追求:大量采用错开不对齐的节奏,伴以短小跳跃式三音列无调性旋律,用单簧管非常规音区吹奏、小提琴不揉弦等乐器法,营造原始气氛——时而幽深神秘、时而咆哮嘶鸣,这是对西方优秀音乐文化成果的一次借鉴。作为全场唯一的一部民乐作品——二胡四重奏《脸谱》(熊晓曲),用四把二胡演绎了中国戏曲文化中“活”的脸谱艺术,这部颇具中国元素的作品在音高上采用la dol re mi sol五音列,非传统的不断变换宫位转调;二胡演奏技法上继承了自刘天华以来的发展成熟的演奏技巧,并运用非常规演奏形式,譬如非音高因素的滑音、用弓根缓慢运弓以求粗厉的噪声、拨揍等等;在曲体结构上借鉴了中国传统 “散-慢-中-快-散”的结构来布局,但在体裁上打破了传统乐器组合形式——用四件同样的乐器写出无限的变化,不得不说这是一部既具有中国元素又突破传统的作品。三乐章作品六重奏《六冲》(马懋玄 曲)用六件西洋管弦乐器演绎中国古老的哲学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六冲”指的是一种有关十二地支的关系,它代表了地支之间两两阴阳属性相同,所代表的方向相反又相克的关系,具体来说,子午相冲、丑未相冲、寅申相冲、卯酉相冲、辰戌相冲、巳亥相冲。作品使用的六件乐器即相合又相克,作曲家在音色变换上做足了功夫,将同属弦乐组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与同属管乐组的长笛、单簧管(兼低音单簧管)、小号作了很精妙的剥离,并巧妙地运用了点描技术,除了持续音之外,其它乐器在一小节之内的出现频度非常高,基本上是一个装饰音换一种音色,这种高强度的音色变化取得了“光怪陆离”的效果。
与上述“文化元素”类作品不同,余下四部作品可以归为“情绪元素”类。单乐章无标题音乐《弦乐四重奏》(聂鑫鹏 曲)没有采用特别的乐器组合,也没有很炫的现代、后现代技法,但非常出色的将一提、二提、中提、大提四件乐器进行优化配置,随着各件乐器之间的应答配合将情绪的起伏和情感的张力交织在一起。此外作品透露出作曲家具备良好的结构感,全曲打破了传统四乐章组织形态,取之以浓缩贯通的布局——慢、快、慢三个段落,这在浪漫主义兴盛时期例如李斯特、舒曼、肖邦、柏辽兹等作曲家的单乐章作品中是很常见的。获2010年“上海之春”大提琴原创作品比赛三等奖的作品《幻想曲》(商沛雷 曲)以及中央音乐学院“211室内乐精品工程”项目委约作品三重奏《追忆》(纪宁 曲)是本场音乐会值得关注的两部作品。前者动、静相宜,是一首自由洒脱、浮想联翩的大提琴、钢琴二重奏,传达出或遐想、或凝神、或沉思、或踌躇的不同情绪;而后者则是小提琴和两组锣的对话,这是整场音乐会唯一一部使用民族打击乐的作品,我们熟知郭文景教授擅长为打击乐写作品,曾发掘过锣这件乐器的多种音色可能性,如他的代表作《戏》、《炫》、《山之祭》等,打击乐部分写得相当出彩。在这部作品中,两组锣通过丰富的音色变化以及富有层次和逻辑的配合,在作品中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中段小提琴奏出京剧旦角唱腔西皮原板的旋律,好像是作曲家在追忆儿时听长辈唱戏的一段经历的碎片,增加了作品的传统元素。笔者认为推动中国音乐的发展,没有创作是不行的,如何激励优秀作品的出现,高质量的作品比赛以及成熟的委约机制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途径,可喜的是这方面的活动越来越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整场音乐会最后一部作品是六重奏《幻想曲二首》(张晨曲),其中第一首为不太快的行板,具有即兴式的自由幻想气质,作曲家主要是在音色上做文章,每件乐器在吹出音头后,都会出现带音腔式的颤音;第二首为活跃、热情的快板,主要在节奏上做文章,固定节奏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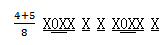 一直贯穿始终,运用复调对位手法,固定节奏型在各乐器声部依次出现,最后汇成一片音响的海洋。
一直贯穿始终,运用复调对位手法,固定节奏型在各乐器声部依次出现,最后汇成一片音响的海洋。
12月5日与第一场音乐会相隔十天,在相同地点,“郭文景师生音乐会”如期上演。作曲家和演奏家以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阵容为主,几乎全部作品为标题音乐,标题具有中国文化元素,民族乐器在整场音乐会占了很大的分量。郭文景教授在开场致辞中重点介绍了《绮梦》、《第一弦乐四重奏》以及他本人纪念汶川地震的作品《飘进天堂的花朵》。开场《绮梦——为古筝、竖琴、笙、圆号和两个打击乐而作》是旅日作曲家胡银岳老师的作品,这是一首融合中国传统、西洋、东洋音乐风味的作品。在节目单的曲目介绍中,笔者了解到作曲家的灵感来自诗人郁达夫青年时代客居日本时的一首诗。相同的境遇不同的年代,一首诗促成了作曲家和郁达夫之间跨时空的对话。乐器编制考虑了中西的对比:古筝对竖琴(弹弦乐器)、笙对圆号(吹管乐器)、民打对西洋打击乐。在音高组织关系上,笔者认为作品多采用中国五声羽调式音阶(la dol re mi sol)以及日本“都节”调式音阶(mi fa la si dol),某些片段甚至是无调性的。在节奏上,作品吸收了加美兰音乐以及中国传统戏曲武场的节奏因素,复节奏对位随处可见。《西风破——为二胡、高音笙、低音提琴而作》(周娟曲)和《临·渺——为短笛、竖琴、5个Tomtom鼓而作》(夏苒曲)都是为三件乐器而写的三重奏,两首作品都有一些突破常规的乐器配置,前一首作品为两件民族乐器二胡、笙以及一件西洋乐器低音提琴做搭配,而后者也用了在室内乐中不太常见到的短笛、竖琴和Tomtom鼓配合。两部作品的主旨不尽相同,前一首作品“西风破”题解为“打破西方音乐的韵律,揉进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所以作曲家充分发挥了二胡和笙——这两种民族乐器独特的音色,通过爵士乐的因素肢解西方艺术音乐,使中国传统音乐、西方艺术音乐、美国黑人爵士音乐三者在一部作品中进行了对话。后一首作品不强调文化意味,而是着重理性的哲学思考:即人与人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越临近越渺远吗?作曲家努力营造渺远和空灵的意境,短笛和打击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红楼梦魇——为人声、弦乐四重奏、单簧管与长笛而作》(杜薇曲)和《长安纪——为琵琶、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钢琴而作》(陈欣若 曲)都是写故事的作品,“红楼梦”、“长安”是两个具有明显意义的文化符号,前者用昆剧《牡丹亭》解构古典名著《红楼梦》,后者虚构了一个发生在唐代安史之乱时的爱情故事。两部作品都分别在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的基础上加入了特殊音色,与故事剧情相符,前者融进了昆剧唱腔,后者采用唐代时逐渐走向成熟的乐器——琵琶。
Lorenzo Restagno是一位对中国文化特别着迷的意大利青年作曲家,他的作品《Freddo》(意:冷)是他来到北京感受到冬日的寒冷,激活了他在家乡意大利北部山区严酷气候感受。作品在双簧管、大提琴、低音提琴的基础上加入了电子音乐以及男高音,极力营造刺骨的寒风以及冷的状态。
郭燕娃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是全场唯一一部无标题音乐,作曲家没有刻意明确作品的文化身份,也没有用先锋的技法,而是用粗厉的笔触细腻地表达了内心情感的激荡。作为整场音乐会压轴之作——郭文景为纪念汶川地震而写的《飘进天堂的花朵——为三组民乐四重奏而作》是一部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全曲共七个乐章,当晚音乐会取其中第一乐章《灾难》和第七乐章《飘进天堂的花朵》。第一乐章用高音吹管乐器的嘶鸣、点状织体和震颤的碎片似的节奏等技术手段描写了灾难降临之后的可怕景象。第七乐章在弦乐声部采用歌唱桂花的民歌旋律,但时常被闯入的管乐器奏出的新材料所打断,象征生命的花朵遭受摧残。
二、
再说感受。
笔者作为普通听众,初步看来两场音乐会的制作情况不尽相同。客观地讲,首先节目单的印制,后一场的更精致,内容更详实,有了作曲家近照、简介以及作品解说,必要的介绍可以加深听众的理解,又不影响听众自由充分的审美想象,良好的节目单制作可以给听众带来愉悦的听赏体验。其次,前一场音乐会中规中矩,后一场音乐会采用了舞台灯光技术,使音乐会的演出形式更加丰富,随着音乐的展开而变换灯光颜色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气氛,在“听”之余给人更多视觉上的感官体验(但也有听众反应灯光切换太频繁、灯光使用太多之后,让人产生了视觉审美疲劳)。再次,两场音乐会基本上保证了较高的演出质量,这要归功于二度创作者,相比较而言前一场音乐会所请的演奏家多是在校优秀学生,后一场音乐会所请的演奏家多是教师,专业的演出队伍(很多演奏家组合都是固定的重奏组)、充分的排练磨合是对演出效果的有力保障。
尽管如此但并不是说,两场音乐会就尽善尽美、完美无瑕了。宋瑾教授撰文称对现代作品的“评判应该以各种创作结果对各自创作目的的‘合目的’程度为标准”[①](2009:P.26),从一个专业评论者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作曲家无论标榜什么理念或者宣扬什么技法,懂行的受众有时并不买账,他们有独立的欣赏现代音乐的标准,也就是说受众听得是音乐,是作曲家实际写了什么,有没有达到作曲家原先设定的意图,有没有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思想上的碰撞以及进行了何种程度的对话,而不仅仅是看看标题、听听曲目介绍就会被作曲家牵着鼻子走。笔者学识浅薄,就这两两场音乐会,具体阐述一下个人浅见,求诸各家批评,也请作曲家参考:个别作品的实际效果并未充分达到作曲家的初始意图,诸如配器中乐器选择问题、某些段落让人思来想去不知所云等等,问题的出现可能是写作的问题,也可能是实际演出并未取得良好效果的原因。例如《追忆》中两组锣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这件乐器的表现力,但笔者并不认为这对实际效果有太多的作用。还有《绮梦》是要突出古筝和竖琴两件中西乐器音色的融合与对比,但竖琴的写法实际出来的结果是“融”大于“异”,声音常常被古筝淹没,同样的问题出在《临·渺》中,这部作品短笛和打击乐写得相当精彩,但竖琴的实际演出效果不尽如人意。《西风破》中借鉴了爵士音乐元素,低音提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用法在某些段落不自然,或许实际演奏出的声音再融合一些会更好。《飘进天堂的花朵》在节目册的曲目介绍中说“这七个独立成章的乐章,可自由组合成六个乐章的组曲、五个乐章的组曲、四个乐章的组曲、三个乐章的组曲和两个乐章的组合形式”,笔者没有听过其它的组合方式,仅仅在演出当晚听了第一和第七两个乐章的组合,但实觉不太“过瘾”,第一乐章《灾难》完了之后没有铺垫直接进第七乐章《飘进天堂的花朵》,容易让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
郭燕娃在《第一弦乐四重奏》的解说词中言“一切作曲技术、手段和形式都是服务于内心情感的表达”,我想两场音乐会的十六位作曲家对于技法的选择,也确实是根据每首作品的特殊要求和自己的审美趣味所选择的。笔者要讨论的是作曲家的选择有没有体现出追寻自己的音乐“母语”,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音乐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中国当代专业作曲家当然是在参照西方作曲技术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自由选择技术手段的,但是否有意识地去追寻作曲家在成长过程中受中国文化熏染而自然形成的内心音乐语言,也就是使用“母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创作群体的文化身份归属。两场音乐会中某些无标题作品,采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如果不是节目册在时刻提醒听者:眼下这是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否则几乎完全听不出民族风格,听不出作曲家的文化身份。对于中国年轻的作曲系学生而言,找寻属于自己文化属性的音乐语言,让自己的创作风格更加成熟是当务之急,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从一定程度上引入民族因素乃是当代中国专业作曲家在西方乃至全球化语境中获得理解和认知的必由之路。
[①]宋瑾:《写什么·如何写·为谁写——当今中国作曲家思想焦点研究之一》——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09/02 P.24-3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