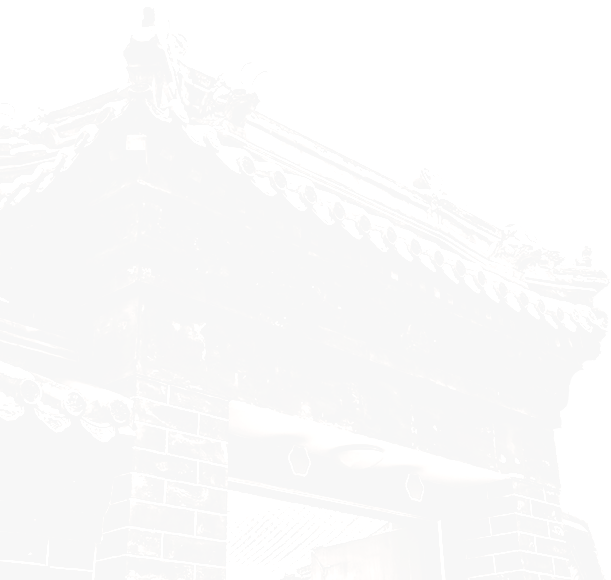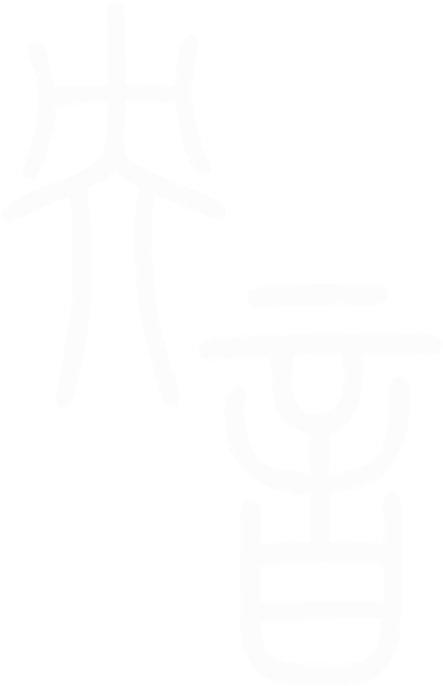时光如刀,切掉了不少岁月,却留下了温暖的记忆。
八十年代初,冬日,南线阁于润洋老师家。小饭桌上,于先生第一次对我谈到音乐美学的“苦海说”,一次有学术温度的深刻交谈,影响了我三十年。八十年代的一个初夏,何乾三老师家,仍然是朴素的小饭桌,那时我是“小罗”,席间,钟子林先生笑着说,“学术也要吃饭的,别光顾着说”。这是一次有生活温度的交流。
1985年,漳州音乐美学会。某日。汪申申老师来到我的房间问:“老罗,去我们那里怎么样?”我大笑道:“今天你是第三个这样问的人了!”三十年后的夏日,中央院音乐美学博士生答辩后,汪老说,“可还记得我们在漳州的对话?你在我家吃完饭就奔西安了”。记忆的温度保留了三十年。
1994年末,香港大学,音乐美学会。与蔡仲德先生深度交谈中国传统问题,那时我激烈,先生淡定;现在轮到学生激烈,我淡定。岁月和学问可以刻划出思想的形象,蔡先生的道德文章,是另外一种温度,一般人不易企及。
2015年,微信圈,偶遇鲍元凯先生,微谈甚欢。他告诉我,1986年我写的那篇评论新潮音乐的文章如何如何在赵沨老的关心下一字不改地刊登在《音乐研究》头条的“内部”信息,言谈中有许多难为人道的趣闻。原来,我还不算“没学”或“霉学”,音乐美学有人间温度啊。
三十年,河东河西。三十年,一个转圜。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不是重复,却是上升。不是感伤,却是温暖。“小罗”变成“老罗”,再变成“罗老”,我初心不变。